研究所簡介
浙江(義烏)商成市場研究所是義烏市商興成市場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設的研究機構。研究所以“興旺專業市場,成就商業地產”為宗旨,專業致力于商品交易市場、專業批發市場的研究。擁有一批精通國內外市場狀況、經驗豐富的高素質專業人才,還邀請了商業地產界及學界知名的專家作為特約研究員或顧問。研究所發展目標是打造民營經濟研究院行業研究所品牌,并成為國內商業地產研究……
業務范圍
聯系方式
趙偉:浙江模式轉型遭外部硬約束——審視浙江模式(之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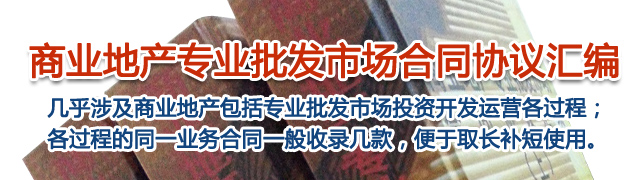 |
浙江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學院博導、CRPE首席教授
浙江市場化體制轉型:以往經歷
浙江經濟是由多個層次的小區域構成的,筆者早先的研究(趙偉,2006)認為:分科層的多層次結構,是中國經濟空間架構的一大特點;從國民經濟到縣域經濟,至少可分出六個區域科層。作為省域經濟的浙江經濟,內部至少可分為三個區域科層,分別為“跨地(級)市經濟區”、“跨縣經濟區”和“縣域經濟”。
歷史地來看,以往30年浙江市場化制度轉型,是在多個科層的小區域同時展開的。其中四個小區域的探索具有開拓意義,并發揮了較大的區域示范效應與區域擴散效應,因而可視為“浙江模式”的原始形態。
第一種是“溫州模式”。
就轉型的路徑或方式來看,溫州模式可稱為“體制外創新”模式。這種模式可作如下簡約描述:留著計劃經濟嚴格監管下的國有、集體等“公有”經濟不去動它,在這個體制之外再造一個系統,這便是非公有制經濟系統,實則為私有經濟;待到這個系統發展到足夠大的時候,再回頭考慮體制內的公有經濟。在溫州,這個路徑的探索幾乎與改革開放同時開始,到1980年代中期已獲成效并引起高層關注,但直到1990年代中期方獲得突破并最終得到官方認可。
第二種是“蕭山模式”,即由前蕭山市(現杭州市蕭山區)開辟的路徑模式。
單就制度轉型路徑而言,“蕭山模式”可稱為“體制內突圍模式”。所謂“突圍”,就是從低效率的傳統企業制度中突圍,變“小公有經濟”為民營經濟。“突圍”開始于1992年末,并在之后短短數年完成。“突圍”的背景有兩個:一個是全國大背景,最重要的是鄧小平“南巡講話”及市場導向的制度改革目標的最終確定;另一個是區域小背景。最直接的背景是,此前政府主導的工業企業體制改革陷入困局。這兩個背景促成了一種改革新思路,地方政府關于這個新思路的表述是: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以轉換企業產權制度為核心,以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為突破口改革公有企業。具體實施辦法是,將大批瀕臨破產的公有企業轉成產權明晰的民營股份制企業或私營企業。改革啟動于1992年11月,歷時5年。到1997年末,全區98.14%的國有、集體工業企業完成了轉制。轉制促成了一大批具有競爭力的民營企業,其中包括萬象集團等后來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一大批民營企業。
第三種是“寧波模式”。同樣就其制度轉型路徑來看,可稱為“內外夾擊生變模式”。具體說,就是在海外與省內兩股力量的夾擊下,促成了體制內公有制企業的改革。改革前寧波的情形既不同于溫臺,也不同于蕭紹,作為沿海地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計劃經濟時期的寧波就是中央計劃關注的重點城市,國有企業比重大,改革難度大。在寧波經濟的制度轉型中,兩股“力量”起了重要的作用:一股是海外“寧波幫”加外資,可稱為“外力”;一股是蕭-紹與溫-臺等鄰近地區的民營經濟。外力方面,以包玉剛為代表的海外“寧波幫”,對寧波地方政府改革思路施加了較大影響,而主要以合資(合作)形式介入的外商直接投資,則對寧波國有企業的轉制,發揮了較大作用。“內力”方面,毗鄰寧波的溫臺以及紹興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無疑對寧波本地民營經濟的發展起了大的示范效應與滲透效應。正是此種“內外夾擊”,促成了民營經濟在寧波的后來居上。
第四種是“義烏模式”,可稱為“體制外市場再造模式”。
義烏模式本質上與溫州模式沒有大的差別,都選擇了體制外創新的方式,但與溫州模式不同的是,義烏的制度創新發端于商品分銷業而非制造業。在義烏,先留著計劃經濟主宰的商品分銷系統不去動它,在這個系統之外,新造了一個民有民營的市場銷售系統。但這個系統的發展過程,則形成了對體制內計劃經濟監管的商品分銷系統的“蠶食”,形成了“民進公退”與“民進國退”的機制,由此不斷擴大著民營系統的發展空間。借助“民進國退”機制,義烏先發展為一個區域市場,后發展成覆蓋全國的市場,最后發展成一個輻射國內外市場的國際小商品市場。與此同時,市場集聚反過來促成了周邊區域的工業化,發展了一個緊密依托體制外市場的制造業,主要是小商品制造業。這個制造業的主流企業,絕大多數為私有企業。
浙江市場化轉型靈魂:民有民營
多層次小區域改革探索的主角,是當地民眾和地方政府,內容與形式豐富多彩。正是這些小區域經濟的轉型探索,匯聚成了浙江經濟轉型探索的大潮,賦予制度轉型的“浙江模式”以其區域特征。
經濟體制轉型的“浙江模式”,應視為所有上述“小區域模式”的融和與空間擴散。不難發現,這些小區域模式的共同指向,莫非兩個詞,即“民有”加“民營”。因此可以認為,民營化或“非公有化”,當屬制度轉型之浙江模式的核心內涵。
就浙江全省來看,區域經濟民營化經歷了兩個大的演進階段:第一個階段從改革開放起步到1990年代初期告一段落,制度轉型的主基調是體制外創新,由此創造了一個龐大的非國有經濟體系。但這個體系的主體組織,主要為“集體經濟”。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浙江全省按經濟類型劃分的工業產值結構為:國有占63.89%,集體占36.2%,私營不到1%。到了改革開放12年之后的1990年,集體工業遠遠超過國有。當年全省工業增加值所有制結構為:國有占23%,集體占61.3%,私營占15.7%。就是說,集體與私營加總的非國有工業比重占到77%。
第二個階段由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為契機掀起,到1990年代中期獲巨大突破。這個階段制度轉型的重心在于體制內“突圍”,即將部分企業由體制內改為體制外,由此實現體制突圍。“突圍企業”主要包括了三種類型的企業:(1)產權模糊的集體企業;(2)“戴紅帽子”的私營企業;(3)地方國有中小企業。“突圍”歷時不到五年,其間絕大部分集體企業被轉成了私有企業,幾乎所有的“戴紅帽子”企業被摘帽。到1997年,全省工業增加值中,純私有的工業企業增加值已占到40.6%,集體工業則下降到36.7%,民營化或非公有化趨向非常明顯。
這里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制度轉型中地方政府的行為。有一種觀點認為,浙江制度轉型中地方政府大多取“無為而治”的態度,這一說法有失偏頗。就上述四個小區域制度轉型實踐模式的形成過程來考察,可以認為,民營化制度轉型中浙江地方政府的行為,大體上有三種:一種是“無為而治”式的,以溫臺模式的形成與發展期間的地方政府行為最為典型,義烏模式其次。另一種是主動出擊式的,以蕭山政府最突出,紹興其次;第三種是順應潮流式的,以寧波為典型。客觀地來說,如若沒有地方政府的有意推動,不僅蕭山模式無從談起,即便寧波模式的形成,也可能要大大推遲了。
無論是無為而治式的,還是順應潮流式的,地方政府的行為都對“民有”、“民營”趨向的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肯定了區域體制市場化的這一核心內涵。
浙江市場化轉型:遭遇外部硬約束?
浙江區域制度轉型的動力機制,帶有自下而上的“倒逼式”鮮明特征。我的研究認為,產業地方化及產業集聚、個人商業才能以及大眾致富強烈欲望等因素一起,對于制度轉型形成了一種自下而上的“倒逼式”壓力機制:個人商業才能與產業地方化要求逼迫基層小區域政府從容忍、默認到鼓勵的變化,小區域的改制與產業集聚逼迫更大區域的地方政府從默認到鼓勵的改革,……,最后這種層層倒逼的力量匯聚到省域層面,促成了全省范圍的制度轉型。
然而客觀地來看,浙江區域制度轉型迄今所突破的范圍仍然是十分有限的。若以國民經濟三次產業作為判斷這種范圍的基本線索,則不難發現,迄今為止浙江市場化轉型,僅在“一個半”產業獲得了突破,在另“一個半”產業,則未有大的作為,體制與別的區域差別不大。突破的“一個半”產業為“二產”和“三產”的非主體行業。說具體點就是制造業和三產中的商品批發與零售、公路及內河航運、餐飲、旅游服務以及建筑等行業。主要標志是,這些產業和行業都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地方民營經濟部門,這是“浙江模式”之“民營化”特征發揮的最突出的領域,也是個人商業才能與產業地方化及其積聚發揮的最大空間所在。尚未突破的“一個半”產業,分別為第一產業(農業)和第三產業的主體行業。其中“一產”受制于全國“一刀切”的農地制度和家庭生產責任制之制度安排,區域改革與創新權限有限,因而缺乏區域創新特色。“三產”之主體行業,諸如金融、保險、主體運輸(從公路網到鐵路運輸,從航空到遠洋運輸等)、電信、電力等等,受到超地方政府力量的控制,制度轉型的民營化與民營主宰的產業集聚無法涉足。
這就是說,區域制度轉型與產業集聚的“倒逼機制”,僅限于地方政府有權處置的產業與行業,超出地方政府權限,“倒逼機制”便無能為力了!
不僅如此,就最近一兩年的情形來看,制度轉型的“倒逼機制”遇到了明顯的外部硬約束。這方面兩個現象最為突出:之一是,迄今尚未取得實質轉型突破的“三產”主體行業的國有壟斷在不斷強化。壟斷行業中的大型國企具有準“上級”政府的影響力,地方政府難以駕馭。這方面尤以鐵路、能源供給、通信以及金融等壟斷行業的影響力為最。別的不說,單是超地方政府對軌道交通建設的壟斷與控制一項,就極大地束縛著區域經濟發展和民生的改善步伐。按理說鐵路等軌道交通是陸上最經濟、最安全、最環保的運輸手段,然而由于超地方政府壟斷,其建設遠遠滯后于區域經濟發展,地方政府被迫成天“折騰”馬路,而無權修建一寸鐵路。之二是,農地改革以及農村改革迄今止步不前。雖然城市里的民有民營浪潮刮了多年,但民有民營對于廣大農民而言依然恍若隔世,多數農民迄今對自己的祖宅所享有的產權都是不完整的。至于耕地產權,就更不能碰了!這些都大大超出了地方政府的權限。
目前來看,在世界經濟衰退和中國經濟回調的大背景下,隨著各級政府刺激經濟財政的形成,審批制悄然回潮,國企財力悄然大增,大型國企借重組、并購等名堂在明目張膽地提升壟斷程度。這一切,都與浙江模式以往路徑所倚重的方式——民有、民營——格格不入。
在這同時還可看到,地方政府的行為似乎也正在發生某些微妙的變化。在發生了紹興江龍老板攜款出逃、臺州飛躍等大型民企危機之后,地方政府出于避險考慮,顯然在加強對民企的干預。與此同時,在各種“保持與上面一致”的口號下,政府以往對民有民營鼓勵的態度似乎正在抽緊,而通過企業黨建、工(會)建、政府融資支撐等方式,越來越多地介入民有民營的經濟實體之中。令人擔心的是,如若抽去乃至削弱民有民營內涵,“浙江模式”勢必將失去創新動力,這一點值得各方去深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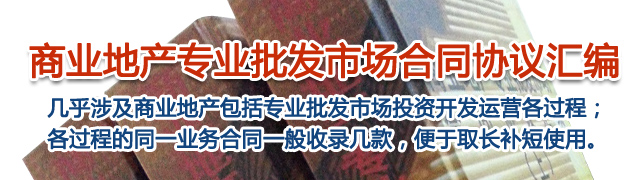 |
點擊次數: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