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我們
聯系方式
武漢漢正街搬遷遭商戶反對 500年市場面臨抉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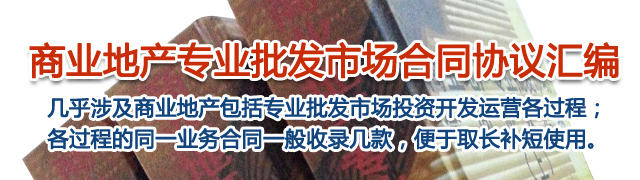 |
 |
從3月中旬開始,漢正街開始進行“綜合整治與搬遷改造”。傳統批發還是現代商業,城市改造如何平衡民生保障?這座有500多年歷史的老市場面臨著新的選擇。
焦慮
劉富民(化名)很焦慮。武漢的天氣逐漸熱了起來,他還穿著一件半新不舊的駝色皮夾克,里面的絨線衣扎在腰帶下面。半瓶“白云邊”下肚后,他開始不停地念叨:“漢正街不能搬啊。”這名50多歲的漢正街商人感到危機日益臨近。
不安的源頭來自3月15日的一次會議,會議由武漢市硚口區宣傳部組織召開。劉富民還記得,會議的主題是關于漢正街“整體搬遷”的民意調查。“沒錯,說的是‘整體搬遷’,調查問卷上就是這么寫的。”為了證明真實性,他還拿出了一張印有“整體搬遷”抬頭的會議人聯絡名單。參加會議的人,除了管委會、區政府的官員外,更多的是漢正街上主要商會和物業公司的代表。
“搬遷”——這個詞讓劉富民們感到格外刺耳。“500年歷史的老街,‘對內搞活’的樣板怎么能說搬就搬呢?”
在街上,劉富民算是個有“勢力”的商戶。他和其他小商人一樣,不修邊幅,不開好車,喝“白云邊”抽“黃鶴樓”。但他有“地盤”——2000多平方米的商鋪。解放前,他的父親12歲就從漢川跑到漢正街當學徒。3年出徒后,父親就在街上最富盛名的“老三鎮”市場開了自己的雜貨店。多年后,劉富民也在街上出生長大,不免耳濡目染。80年代初,市場重開后,劉富民再度開啟家族生意,從針頭線腦、襪子鞋墊開始,摸爬滾打30年,創下了現在的家業。按照均價2萬元/平方米計算,他的鋪面就值四五千萬元。但如果漢正街搬遷,這些資產就一文不值了。
“民意調查”的會議充滿了火藥味。商戶代表們情緒激動地反對任何關于“搬遷”的提法,組織方希望參會商戶們再選出代表發表意見,但是遭到了拒絕。沒有人打算中途離開或者置身事外。最后妥協的結果,將最后一個小時作為自由發言的時間,每名商戶以5分鐘為限。
政府希望通過搬遷、整頓消除市場的火災隱患、交通梗阻,進而改變“現場、現貨、現金”的傳統交易模式(三現模式),將喧鬧、蕪雜的批發市場改造為秩序井然的現代商貿旅游區。而商戶們則認為,火災與交通問題主要根源在于政府管理不善,取消傳統的“三現模式”不具備條件,“支持整頓,但是堅決反對搬遷”。會議最終不得不在爭吵中結束。
5天之后,3月15日,武漢市漢正街綜合整治與搬遷改造小組正式發布公告,“即日起啟動漢正街綜合整治和搬遷改造工作”。漢正街2.56平方公里被劃為拆遷區、在建及建成區兩大塊。拆遷區整體搬遷,在建及建成區則依法整治、全面改造、轉型升級。
三五年來關于搬遷的傳聞,就像“狼來了”的預言,在街頭飄蕩,如影隨形但從未坐實。熙熙攘攘,利益往來,生意照舊。但現在兩萬多商戶的心頭卻輕松不起來。
劉富民的好朋友胡波(化名)也是街上的大戶。他的家族是恢復市場后的第一批個體戶,目前家族究竟有多少鋪位,估計胡波自己也說不全。與劉富民不同,他已經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整頓搬遷”的寒意。
胡波在漢正街東富商城有4個鋪位,這座市場專營塑料制品和玩具。4月初,胡波收到了東富商城進行防火改造的通知,他所在的C棟要在4月底關閉。按照胡波與租戶的協議,要提前兩個月確定續租事宜。4個鋪面的租期在5月底結束,但突如其來的變化使雙方都措手不及。租客們不知道再到何處去找鋪面,客源將大量流失。胡波也不知道市場會何時重開,他說“即使給我房租,我也不能收了”。
市井
每天早上5點多鐘,漢正街的生意就開始了。“打貨”的客人從各個方向進入市場,大包小包地拖走各種商品,以趕在開門前補充貨架。傍晚收檔后,街道立刻成為夜市,批發市場變為零售市場和人頭攢動的小吃街。即使到深夜,沿江大道仍舊馬達轟鳴,汗流浹背的工人把貨物塞進卡車。
漢正街的牌子就立在晴川橋下,這里是街道的入口。道路坑坑洼洼,下過雨后一片泥濘,很多地方不得不墊上碎磚頭。灰塵在陽光下飛舞,空氣中彌散著一股洋灰味兒,間或混雜著垃圾的酸臭味,布匹、鞋帽、襪子、發卡、鍋碗瓢盆分門別類地堆在檔口,充斥著一種廉價的富足。
商品價格低廉,貼著五花八門的牌子,主要針對鄉村鎮集市場,常能看到“山寨式”的品牌創造,比如“美·摩根保羅”的女裝,或“路易·鯊魚”的皮箱。
街上到處是擁擠的人群和門面鋪位,許多赤膊的搬運工人,大聲叫賣的伙計,在過道睡覺的孩子,討價還價的顧客。在最少的地方擺下盡可能多的鋪位,擺放盡可能多的商品,并且盡可能地降低商品的成本,這是漢正街永恒不變的法則。商鋪如同中藥柜子,密密匝匝地塞進了大大小小的街市和樓宇。每個檔口里都堆滿了商品,客人看上什么,直接雇扁擔和板車拉走。
老板們湊在一起,在路邊支起麻將桌,坐等客戶上門。電線桿子上貼滿了鋪面租售、招工的廣告,最特殊的是要“狗肉賬”廣告:“沒有收不回的賬,只有不想要的賬。”“撞了,撞了!”搬運工拉著堆滿服裝的拖車,在貨車、人群間穿梭。逼仄坑洼的街巷、老舊昏暗的大樓、燈光絢爛的商廈……人與車、新與舊、亂與雜在這里繪制出市井百態。
通常所說的“漢正街”并不單指一條叫做“漢正街”的街道,而是包含這條東西向大街為中心,在漢水和長江匯合處南北延伸的一大片老城區。它由近460條街巷組成,核心區域占地約1.6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20萬。正如名字所傳達出的信息,“漢正街”乃漢口之正街,歷史上就曾經是漢口的中心區,也是武漢城市文化的搖籃之一。
漢正街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朝萬歷年間。在水運和商業的驅動下,漢口的街市沿著漢水流向自然形成并延伸,漢正街市場形成。沿江從西至東,出現了宗三廟、楊家河、武圣廟、老官廟和集家嘴等眾多的碼頭,為商埠吞吐、集散物資。由于水上交通便利,沿街店鋪行棧日益增多,貿易往來頻繁。之后,各地富商大賈集聚于這塊風水寶地。再后來,青磚瓦舍取代了茅屋竹籬,四鄉流民成為市場取之不竭的勞力資源。到清代康熙、乾隆的經濟發展鼎盛時期,漢正街已成為“漢口之正街”。
20世紀初,隨著漢口開埠,租界設立與鐵路的開通,漢口商業中心逐漸下移至長江岸邊。漢正街則演變成小商品市場。“文革”期間,漢正街曾被更名為“興無街”,所有市場都被關閉,個體商人不得不另謀職業。直到1979年,漢正街市場恢復,第一批103戶個體經營者重新出攤。由于武漢獨特的地理位置,漢正街市場一度成為全國性的小商品批發中心,被稱為“天下第一街”。
時至今日,這一區域依舊保持著相對傳統的空間格局。漢正街的形態如同一條魚,魚嘴在晴川橋,魚肚子是漢江邊的沿江大道,魚背是武漢的商業中心中山大道,魚尾則甩到江漢橋。東西貫通的漢正街,就是魚身上的那根主刺。
在命名上,漢正街遵循著一個歷史習俗,即東西走向與漢水平行的稱為“街”,南北走向與漢水垂直的為“巷”。主要的“巷”都是一頭扎在漢水里,與漢水碼頭同名。巷頭原先還設置有寺廟,表達鎮水和祈求平安之意。這些沿漢正街主脊南北展開的平行小巷,如同魚刺般密集,則是漢正街的血管和紐帶。
細密的小巷與主街交織,形成了層層疊疊的集市。歷史上,正街上的店鋪,主要是大商號的門市、倉庫和會館,沿著河街則是各種分工明確的貨物碼頭、密集的寺廟與集市,堤街曾經是工人、錫匠、大眾茶樓聚集的地方,而垂直于漢正街的是那些致密的魚骨式商住混合特色商品批發街巷,夾雜著娛樂和消費場所。
盡管由于政治運動中斷,但今天漢正街的格局仍舊維持著曾經的歷史脈絡。上世紀80年代末期,漢正街開始不斷地進行舊城改造,利濟路、多福路等南北向道路被拓寬,一部分老棚戶區被拆除,建立起了一系列的商住并存的專業市場。每一個產業都有若干自己的專業市場,并都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
但大量老街巷與舊房屋依舊存在,成為高樓大廈的背景與底色。這些鋪面連接著鋪面,如同人體血管一樣密密麻麻,低矮的鋪面不斷擠壓人行通道,很多通道只能并排兩人來回。電纜電線編織起一張蜘蛛網絡,并成為居民的晾衣繩。傍晚時分,居民們把煤氣罐搬到街邊做飯,整條巷子里就彌漫著辣椒下鍋后的嗆人氣味。
批發生意有兩大特點:第一是同業扎堆,方便客戶貨比三家;第二是交通方便,組織靈活,既能大進大出,也能化整為零。由于街道狹窄、人流稠密,漢正街形成了獨特的物流體系。扁擔與推車是物流的末端,這些挑夫們負責將貨物從門店運到江邊的貨運公司。沿江大道至友誼南路一線則是物流公司的天下。白天,老板娘們在路邊支上一把陽傘,接收挑夫們搬來的零散的貨物,晚上則裝上大卡車,運到特定的城市。
以現代商業的標準,漢正街存在空間上的局限。區域一邊臨河,無法修建太寬的馬路,另一邊的狹窄街巷限制了大宗貨物的出入。在商圈周邊主路上,貨運物流的堆積和擁堵成為這里最大的交通和消防隱患。白天,物流公司的卡車停在街面上,一些商人趁機建造了大片簡易的倉庫和民房出租盈利。在漢正街,一切自發的商業活動都是同一類利益驅動下建設起來的。但是,這種互相依靠共生的高密度業態,以及多年的歷史積淀,共同激發了蓬勃的人氣,使這里永遠川流不息。
蜷縮在老房子里的店鋪,嘈雜的人聲,擁擠的車道,推著板車來回卸貨的工人,還有掛在街頭“杜絕一切火災隱患”的紅色條幅,都顯示著這里的破落與繁華。而時不時出現的紅色“拆”字,則提醒著這里未來的命運。
買賣、物流、倉儲、加工、居住、吃喝拉撒……都集中在這不到1.7平方公里的區域內。三教九流,五方雜陳,熱氣騰騰,分工明確。現場、現貨、現金的交易模式,混亂之中也遵循著自己的秩序與江湖規則。
在官方看來,混亂的交易環境、低端的經營模式、落后的市政設施,使漢正街逐漸成為城市的潰瘍。而在劉富民們看來,這種“亂”正是漢正街的核心價值,體現了漢正街歷久彌新的生命力。“不亂不鬧,怎么會有人氣?怎么會有市場?”
爭執
按照官方思路,漢正街必須要進行提檔升級。
如何升級?通俗地說,就是要做到“四個轉變”:市場主體上,由個體戶變企業,目前工商部門在漢正街區域已不再核發個體工商戶執照;市場形式上,由批發市場變成現代商城,統一物業管理;交易形態上,由現場、現金、現貨的“老三現”變“新三現”,即現代化的電子商務、現代化的商貿一體和現代化的遠程批發;歷史文化上,漢正街文化由概念變實在的元素,選取有代表性的歷史遺跡,復原明清風貌。
漢正街該往何處去?每年武漢“兩會”上,這個問題都會以不同形式被提出。但方向在哪里,并沒有共識。爭論之中,生意照舊。
傳統的城市環境如何適應現代化的發展,是一個艱巨而普遍的難題。問題在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人們往往更樂于忽視它、繞開它。于是,發展的滾滾車輪往往還來不及判斷,就已經別無選擇地沖過了十字路口。而發展總是伴隨著巨大的歷史慣性,如果就像扳道岔一樣改變漢正街的運行軌跡,往往需要一個契機。
今年1月17日,漢正街西端的一處門面失火,造成14人死亡。火災成為引爆這場變革的導火索。武漢市代市長唐良智考察后說:“不看則已,你看了一定睡不著,隨便一點火星就報廢了,你跑也跑不掉,所以一定要下決心。”
但劉富民、胡波與很多商會的會長們并不認同政府的邏輯。“武漢廣場不也是現場、現貨、現金交易嗎?為什么那里沒有著火?”胡波說,“漢正街64個專業市場都沒有發生過火災,著火的是那些老市場、由居民戶改造的鋪面。這是一個市場管理的問題。”
2005年末,漢正街上一處作坊因機器超載引發大火,隨后政府陸續將6000多家服裝作坊遷到了區外。自此,漢正街的生產功能被剔除,再也聽不到機器的轟鳴聲。但是,今年“1·17”大火恰恰是發生在一處小作坊內。“為什么這種服裝作坊又回來了?為什么沒有人追究監管的責任?”胡波說。暨濟皮具商城商會會長周樂喜說:“我們支持改造、防火檢查,但是反對搬遷市場。”漢正街有1600戶物流公司,但是其中有證的只有500戶,無證經營一直得不到處理。而假貨多的問題,商戶認為這是工商部門的職責,跟搬遷無關。
對于防火、交通的改造尚屬市政范疇的城市更新,但是對于交易形態的改變則觸及到了漢正街的商業模式。政府希望借助整頓市場,改變“現場、現貨、現金”模式,從本質上把漢正街從一個“烏煙瘴氣”的傳統批發市場,改造為一個井井有條,結合現代物流、倉儲甚至電子交易的新型商業。
硚口區區長胡勤華認為:“如果我們總是拘泥于《人民日報》1982年8月28日社論《漢正街小商品市場的經驗值得重視》這樣一個調子,不重新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未來漢正街肯定是沒有出路。”
但很多商戶認為這樣的改變不切實際。“漢正街絕大多數的商品針對的是農村低端市場,客戶是那些集鎮上的小老板。他們下一次單,幾件、幾十件,看中了就拉走,賣完了再來,既不會用電腦也沒有信用卡,如何讓他們適應新的交易模式?”周樂喜說。
盡管漢正街的稅收與創造財富的能力并不高,但商戶們認為并不能因此否認它的社會價值,不該用GDP來評價漢正街。“漢正街吸納了大量的低端就業,一個商鋪就是一家子的生計,是社會的穩定器。”胡波說。漢正街目前約2.6萬商戶,按照每戶5人計算,就有約13萬直接從業者,而為商戶們服務的卡車司機、扁擔工、餐館、物業公司的人數還會繼續放大。
劉富民相信,漢正街市場的存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歷盡劫難但生命力頑強。“乾隆時期,一把大火燒了江邊上百條貨船,漢正街沒有倒;1938年武漢保衛戰,漢正街又被日本人燒成一片灰燼,后來一樣開市;1944年,中美空軍反攻把街上老三鎮市場炸平了;到‘文革’時候,小商人成了投機倒把的犯人,漢正街依舊不死,還有人做地下的生意。活躍的市場不是靠人為規劃出來的。”
這種不信任與不安全感,在某種程度上源于對商業環境與小商人命運的焦慮。“我們的利潤本來就薄,現在各種稅收、負擔費用攤派越來越重。”劉富民嘆了口氣說,“每年我被攤派的訂報費就有5000多元。”
角色
心緒不寧的時候,劉富民會去看望一下“選哥”——漢正街上的標桿人物鄭舉選。
今年71歲的鄭舉選已經退出市場多年,在漢陽一處臨湖的小區中頤養天年。他目不能視,戴上一副墨鏡,身板健壯,生意響亮,花白的頭發梳到腦后,仍有大哥風范。鄭舉選一生命運多舛,而他的經歷,也體現了漢正街輝煌時期的商業模式。
“說好聽的,我是做小買賣的;說的不好聽,我在漢正街討了一輩子飯。”鄭舉選對我們說。
1940年鄭舉選生于漢陽縣侏儒鄉下。6歲那年,因為鄉下鬧天花,他的兄弟姐妹夭折。鄭舉選雖活了下來,但卻傷了眼睛,年輕時還能輕微看見東西,幾經折磨后,就徹底失明了。
1946年鄭舉選隨父母從鄉下遷居到漢正街。因為眼睛不好,他也沒讀過什么書,十六七歲就跟父親擺攤學做小生意。“我是殘疾人,幾乎沒在單位上過班,不想給別人添麻煩,就想擺小攤,自食其力,做一個平常的生意人。”鄭舉選說。
上世紀60年代初,漢正街還保留著商埠風貌。雖然商品奇缺,但做生意并不違法。街上有3000多戶商鋪,鄭舉選也有自己的營業執照。“那是我第一個身份——小商小販。”
好景不長,“文革”開始后鄭舉選的小商販“身份”就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為了吃飯,鄭舉選不得不偷偷摸摸繼續他的地下生意。他拄著竹蒿子,挎一個包,里面裝點紀念章、五角星、線索子、花邊、氣球等小玩意,在街上晃悠。有人買就碰一下膀子,三言兩語成交。“和我做生意的很多都是盲人,不能算命,不能唱戲,不做點小生意就只能餓死了。”鄭舉選的地下生意自然瞞不過“打辦”,家里多次被查抄,他也經常被拉到學習班接受處罰和批判。“這時候我的身份是‘殘渣余孽’。”鄭舉選說。
鄭舉選是個講義氣的人。在學習班和看守所,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下來。“和我做生意的都是可憐人,我怎么能交待別人。”他的問訊筆錄里總是那幾句老話:“貨從哪里進的?”“街上進的。”“都賣給哪些人了?”“看不見,不認得。”“賺到的錢呢?”“滾到貨里去了。”“貨呢?”“被你們收了。”鄭舉選在漢正街的名氣也越來越大,都知道有一個硬氣的“麻瞎”。
學習班里也有被槍斃的“班友”,罪名是倒賣票證、金額過萬。鄭舉選對自己和周圍的朋友說,為了活命,可以偷偷摸摸做點針頭線腦的小生意,但切莫倒賣糧票、油票、肉票甚至煤球,倒賣這些就是破壞國民經濟和人民的正常生活,是最大的政治問題。
1979年6月,在經歷了18個月的牢獄生涯后,鄭舉選再次被釋放。這時漢正街市場恢復,工商局的干部找過去的經營戶做工作,鼓勵街上的無職業者就地就業。這一年的11月初,在漢正街最大的國營商店“謙祥益”對門的公安巷口,鄭舉選搬塊破門板,往兩個矮凳上一擱,算是出攤了。他是漢正街重整之后第103個“個體戶”,從此有了新的身份,他也成為了這個市場的精神領袖。
80年代是漢正街的黃金時代。一方面,社會物資匱乏、流通不暢、產銷不對位,國營工廠里積壓了大量銷不出去的商品,而民間卻買不到東西;另一方面,當時國內交通尚不發達,而武漢地理位置居中,水旱碼頭交通便利,于是唯獨漢正街上的生意可以“買全國、賣全國”,成為了全國性的小商品集散地。
一家針織廠的垃圾堆里有大量廢棄的勾針,鄭舉選就拖回來,請人稍加打磨就成了婦女手里的編織工具,城里鄉里都好賣。武漢打火石廠積壓了大量的打火石,鄭舉選都包了下來,賣到四川去做打火機,因為四川農村男男女女都抽旱煙,打火機是必需品。靠著15元的起步資金,只做了不到3年,他就成為街上的萬元戶。
形勢比人強。靠著拾遺補缺,溝通有無,然后貨通天下。鄭舉選們的生意經后來被總結為“漢正街模式”。而鄭舉選盡管是個盲人,但是記憶力驚人,幾百種商品,幾千個規格,他都能熟記在心。時至今日,下象棋是他賦閑后的最大愛好,完全心算,車來象往,一盤棋了然于胸。
盡管鄭舉選此后榮譽無數,成為“時代模范”,但他仍舊謹小慎微,恪守本分。“我一個人納稅抵得上十幾個健康人,我從來不會少交國家一分錢。我只想踏踏實實做生意,不想因任何問題再被找麻煩。”鄭舉選說。
小商人的日子還是過得不踏實。
傳統
作為暨濟皮具商城商會會長,周樂喜是打算在漢正街長期扎根下去的。在整個80年代,這個湖南邵陽人挑著擔子走遍天下。最初他走街串巷修鞋,最遠一趟,從老家邵陽靠一雙腳板走到了貴陽。后來他開始賣書包,因為邵陽有個生產書包的工廠,老鄉們拿貨方便。于是拿上200塊錢當本錢,扁擔上掛滿了書包,走到哪兒賣到哪兒。賣完了再回家取貨。一天賺上一二十塊錢,比在家種地算工分好上太多。
幾百年前,周樂喜的同鄉們就沿著長江放木排到漢口,在漢正街上聚族而居,壟斷了木材和紙張生意,目前還留存下了寶慶巷。1987年,周樂喜挑著擔子來到了漢正街,看著九省通衢客流如織,就再也不想走了。
那是漢正街的黃金時代。在武漢燥熱的天氣里,外來戶周樂喜憋著一身力氣,唯有拼死苦干。每年七八月份是服裝淡季,攤位的租金便宜。而此時恰逢學校放假至開學,是書包的銷售旺季。周樂喜就利用這個空當,以低廉的價格租下攤位,擴大銷售。等9月開學后,他再退掉攤位,重現回到街上當貨郎。
到了1992年,他終于在一個商場地下室租上了攤位,生意也從書包擴展到了箱包皮具。小本生意,雇不起人,全靠自己。他的住處也是倉庫,每天睡在拉桿箱上。半夜貨車司機送貨,他都要起來開門,點數簽收,一晚數次。天不亮,市場開門,他又要撐著睡眼開門迎客。
90年代,漢正街正經歷著一次大變化,專業市場開始成為主角,商戶們不再什么賺錢一窩蜂而上,而是確定自己的發展方向。于是市場內部開始合并同類項,服裝、鞋帽、箱包、皮具、塑料、玩具、文具、禮品……同一類的商戶聚集在一起,組成專業市場。
周樂喜跟著其他皮具商人租到了華貿商城。他的生意雖不大,但是為人熱情,具有同業精神,早早地就在箱包商戶中組織了湖南商會。做箱包生意的湖南人雖不多,只有三十來戶,但很抱團,隔三岔五地開會,大事小事一起商量。周樂喜組織商會與物流公司商談合作,首次拿到了20萬元的貨運押金。不僅壓下了成本,還降低了風險。后來曾有客戶被運丟了一車貨,最后迫使物流公司照價賠償。
批發生意的特點并非單打獨斗,講究的是同業聚集的密度和質量。眾多商戶形成一個穩定的經營群,依靠整體的力量吸引更多的采購者。2005年,周樂喜覺得此前大家同租鋪面的方式遇到了很多問題:“漢正街的商場越開越多,依靠最初低租金和優惠吸引租客,這就造成我們商城商戶不穩定,最終損害整體利益。”
有恒產者有恒心,這個道理他是明白的。于是他又聯合了浙江、武漢商人,一共兩三百戶,共同購買了剛剛建成的暨濟商場,共同組建了新的箱包皮具批發市場。周樂喜自己也貸款買了兩個檔口,當初每平方米不到1萬元,現在價格已經翻倍。經過近20年的打拼,周樂喜從一個挑扁擔走街串巷的貨郎,終于成為有產權的小老板。此中甘苦,如魚飲水。
就當周樂喜們從一個無產者變成有產者后,他們發現自己面臨著一個窘困的現實。如果漢正街搬遷,那他們舉債購入的商鋪則失去了價值。而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箱包批發行業越來越難做。武漢本地沒有箱包行業的生產基地,周樂喜們也沒有產地優勢。批發商從河北白溝或廣州進貨,賺取二道販子的中間利潤,能有10%已屬難得。商場中每年都要淘汰近1/3的商戶。行業如此脆弱,禁不起任何折騰。
周樂喜是希望留下來的商戶,他代表了漢正街上頑強的傳統商業力量。這里不僅有他的產權,另一方面,他花了多年的精力才完成了一次傳統批發業的整合,依靠同業聚集形成了人氣。如果漢正街搬了,重新聚合人氣又要多少時間呢?已經苦拼了快30年的周樂喜,心中沒底。
分化
在最近的10年中,“天下第一街”的光環逐漸退去,傳統的批發生意越來越難做。
一方面,全國性的批發市場陸續建立:北有石家莊,南有廣州,東有杭州和義烏,西有成都。漢正街被四面圍住。今日物流交通與1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武漢的交通中心地位已經下降。“買全國、賣全國”的模式不復存在,漢正街下降為一個區域性市場。另一方面,零售業的運行本質發生了巨大變化,中間商作用降低,商業信息更加透明,終端零售直接對接廠商。傳統“二道販子”的生存空間被壓縮。批發市場需要上游制造業支持,而江浙、廣東集中了大量小商品、服裝廠商,產業鏈完備。義烏與廣州兩大市場已經成為了國際性的批發中心。
如果說傳統的批發行業是靠信息不對稱和交通不便賺錢,那么新型商業則是依靠提高產業鏈的效率來牟利。
90年代初期,本地人鄭斌開始在漢正街上擺攤,他正好經歷了漢正街的轉折時期。“最初做生意,街頭一個價,街尾一個價,街頭買街尾賣就可以賺錢。老板們什么都做,社會上什么都缺,尤其是低端商品,也不在意質量問題,只要便宜就行。”鄭斌說。
90年代末期,鄭斌開始走專業道路,先是只賣服裝,然后是女裝、少女裝,最后鎖定到了孕婦裝。此時服裝市場正經歷著巨大的變化。“以前產品周期長,18歲到38歲都穿一類產品,全國穿一種顏色。隨后,產品的更新周期越來越快,市場越分越細,幾天一款衣服就過時。開始還有時間貼自己的牌子,后來都沒時間貼牌直接發貨。如果賣羽絨服,碰上暖冬,又押錯了寶,成了老款,就要虧本賣了。”鄭斌說。
他發現盡管女裝逐漸繽紛多彩,但孕婦裝長期就是兩種——背帶褲和踩腳褲。于是就開始結合流行趨勢做孕婦時裝,把孕期分為若干階段,根據身形推出不同產品。這個精明的武漢人為了摸清市場容量,還專門去計劃生育辦公室了解每年的出生率。
對于漢正街的發展,鄭斌有強烈的危機感:“漢正街市場沒有產業支持,也就沒有長遠發展,這么多年來一直是無根的市場,只能當二道販子。以前全國交通不便,還需要武漢中轉一下,現在這個情況不存在了。”他不想在漢正街的老路上走了。
去年,鄭斌注冊了自己的孕婦裝品牌,一頭開始介入生產,給制造工廠提供圖樣、版型;另一頭,營銷自己的品牌,建立自己的下游銷售網絡。他還開了一家網店做網絡銷售。“理想的模式,我通過自己的銷售網絡了解市場需求,然后向生產商下達生產指標,以銷定產,實行訂單管理。”鄭斌說。
漢正街的環境,也讓生長于此的鄭斌感到愈發不適。“現在漢正街寸土寸金,物流不通暢,缺乏發展的空間。我的貨源來自全國各地,老板跟物流公司關系不好,貨就進不來。”鄭斌說,“大客戶走進漢正街,看到亂糟糟的樣子,也留不住。”
漢正街市場恢復30年后,經營者的分化不可避免。一邊,面對廣大農村市場的傳統商業模式依舊頑強,傳統批發的生命力猶在;另一邊,不安分者想要擺脫“二道販子”的薄利,與現代商業對接,期望在新的平臺上開疆拓土。
武漢的“砧板大王”朱仕香就離開了漢正街。1984年他開始賣砧板,做一塊砧板賣一塊,最初規模很小,每天騎車向武漢三鎮的餐館飯店推銷砧板。當時武漢最大的亞洲大酒店、長江大酒店這樣的高檔酒店也漸漸成了他的老主顧。日積月累,朱仕香逐漸壟斷了武漢90%的砧板市場,一年可以賣幾十萬塊。
2006年,生意做大的朱仕香開始向縱深發展,依托砧板進入酒店用品市場。與賣砧板不同,銷售酒店用品需要大量的展示空間,各種鍋碗、刀叉少說有上千種,規模大的銷售商需要有上萬種商品擺出來。講究的是琳瑯滿目、五光十色。但漢正街的草根味與高檔酒店的氣質完全相左。“即使有高檔貨,你往那個寒酸的店里面一塞,人家就看不起你了。”
為了賣酒店用品,朱仕香需要更大的空間,于是就在新的漢口北市場買下了3000多平方米的鋪位。他不想再守著漢正街,也不再留戀賣砧板的利潤。他需要更堂皇的地方,要更多地展示自己,去爭取大客戶,尤其是那些高檔星級酒店的采購經理。
盡管在新的市場必須要熬一段時間,但是令朱仕香滿足的是,他的鄰居也都是酒店用品的大品牌。他覺得自己終于離開了縣運動會的賽場,開始站在了全運會甚至奧運會的跑道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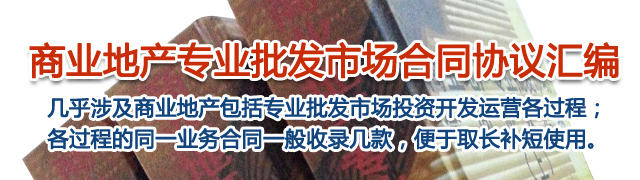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