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我們
聯系方式
溫州“資本自由行”背后的真命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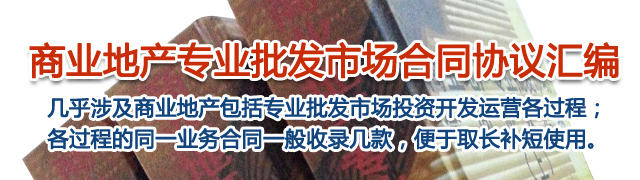 |
 |
●溫州民間資本這些年以“鯰魚”的形象,攪動了整個市場,成為中國民間資本的代表,它的一舉一動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標識意義。如果僅僅從抑制民間資本無序流動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并沒有理解這一金融創(chuàng)新政策出臺的真正意義。
●為民間資本“泄洪”的背后,其實做的是經濟轉型升級這樣一個大課題。在民營經濟的發(fā)展上,溫州一直是一個先行者。通過金融改革,如果能夠把豐沛的民間資本引導好的話,那對于整個中國的民間資本的轉型發(fā)展都將產生示范意義。
●主持人:本報記者 支玲琳
●嘉 賓:史晉川(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
支玲琳:規(guī)模龐大的溫州民間資本的流向,一直牽動著各方關注。近日,隨著《溫州市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方案》的頒布,溫州民資又將首嘗個人境外直接投資。這些年來,以溫州為代表的國內民間資本,似乎總也擺不掉“炒作”“投機”等負面形象。如今境外“資本自由行”的開放,究竟能帶來怎樣的改變呢?
史晉川:這其實在意料之中。我現在受托正在做的一個課題,就是關于溫州區(qū)域性金融創(chuàng)新。除了溫州個人境外投資的試點之外,今后可能還有一系列的舉措將陸續(xù)推出,諸如溫州地方金融機構的改革和發(fā)展,溫州直接融資市場的建立健全(設立風投、產業(yè)基金),溫州在利率市場化方面的率先改革,等等。目前所推出的“資本自由行”,只是先行先試的一個舉措而已。
溫州民間資本這些年以“鯰魚”的形象,攪動了整個市場,成為中國民間資本的代表,它的一舉一動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標識意義。因此,這次放開個人境外直接投資會引發(fā)外界諸多關注和揣測,也在情理之中。但要知道,溫州在上世紀80年代就是我國金融改革的實驗區(qū),也是中國民營經濟的橋頭重鎮(zhèn),如果僅僅從抑制民間資本的無序流動、怎么讓民間資本“不干壞事”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我認為并沒有理解這一金融創(chuàng)新政策出臺的真正意義。
支玲琳:那么政策的真正意圖是什么?
史晉川:要解讀中國的民營經濟、民間資本,溫州是一個非常好的樣本。通過梳理溫州的經濟發(fā)展、資本形態(tài)的變化,我們可以大致看出中國民間經濟發(fā)展的三階段。
第一階段,通過商業(yè)流通領域來形成資本原始積累。比如著名的橋頭紐扣市場、“雞毛換糖”、義烏小商品市場,這在改革開放初期是非常領先,也是非常典型的。
第二階段,通過商業(yè)流通領域完成原始積累后,將資本投入制造業(yè):原本是賣紐扣的,現在去制造紐扣;原本是賣打火機的,現在去制造打火機,民間辦廠如春潮涌動。這種從商業(yè)資本向產業(yè)資本的轉變,成功實現了資本轉換,也促進了區(qū)域經濟的發(fā)展。
現在我們所面臨的,正是第三階段。傳統(tǒng)的制造業(yè)領域本身需要轉型升級:要從傳統(tǒng)制造業(yè)向國家新興戰(zhàn)略產業(yè)發(fā)展,從傳統(tǒng)制造業(yè)向現代服務業(yè)轉變,從傳統(tǒng)制造業(yè)向先進制造業(yè)提升。這種轉型升級,僅僅靠大量分散的中小產業(yè)資本單打獨斗很難完成。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就棄實業(yè)而去,轉向了市場投機。一來,擾亂了市場秩序;二來,也令實體經濟失血。據我們估計,溫州游離于實體經濟之外的投機性資本,大概有6000億-8000億元。這個時候,非常需要有新的融資平臺、融資方式,將這些小的資本積聚成規(guī)模金融資本,再反饋回產業(yè)領域促進產業(yè)轉型升級。所以,無論是現在允許個人直接投資海外實業(yè),還是接下來要推出一系列金融創(chuàng)新舉措,要做的其實都是這樣一件事:要讓民間資本重歸實業(yè)、回饋產業(yè)。
另一方面,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的必然要求。要實現產業(yè)升級轉型,僅僅靠自己的企業(yè)家、現有的資源,實在力有未逮。但通過以民引外、中外合璧,就能使我們的民間資本和國外的產業(yè)資本結合起來,使新的生產要素、新的產業(yè)升級途徑,能夠為我所用、所借鑒,使得以溫州為代表的民營經濟在新的開放格局中,形成產業(yè)的轉型升級。我認為,為民間資本“泄洪”的背后,其實做的是經濟轉型升級這樣一個大課題。
支玲琳:盡管每人每年2億美元的投資“上限”可謂尺度頗寬,但《溫州市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方案》有非常明確的限制,即只準投資實業(yè),不準炒股炒樓,從中可見政策之苦心。但問題是,經濟人講的是實際,最終影響資本流向的是投資回報率。有句話說,“投資如虎、地產似豬、主營像牛”。已經被炒房、炒煤“寵壞”胃口的民間游資,如何才能吸引它們重回“慢牛”的實業(yè)領域呢?
史晉川:對于那部分民間游資來說,盡管過去獲得了一定的收益,但隨著市場經濟的日漸規(guī)范、宏觀調控力度的日益加大,風險正在不斷累積。比如溫州“炒煤團”,經歷了山西當地煤炭企業(yè)重組的風暴后,損失不小。按照單礦不低于90萬噸、集團不低于300萬噸的產能標準,幾乎沒有一家溫州資本投資的煤礦達到這個規(guī)模,所以溫州民資將近500億-600億元在山西的煤炭行業(yè)的投資,結果卻成為被整頓、被整合、被兼并的對象。而在兼并過程中,在采礦權補償、其他一些投資補償方面也有一些分歧和意見。再如“炒房團”。過去溫州資本在全國一二線城市分布非常廣,但隨著房產調控的風聲日緊,房地投資的風險正在累加。尤其是如果想獲得暴利,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再看海外投機,溫州“炒房團”在迪拜樓市被套30多億元,付出的學費不能說不慘重。可見,無論是資源性的煤炭行業(yè),還是金融地產行業(yè),以溫州資本為代表的民間游資所面臨的限制和投機風險正越來越大。這一切都表明,民間資本轉型發(fā)展已經迫在眉睫。
當然,對于這部分投機性較強的資本來說,單單靠允許海外直接投資,不可能完全扭轉其中大部分資本的流向。而且,如果只是單純的資本流出、單打獨斗,其實也不會產生太多的實際價值。只有把“走出去”和國內的金融改革,新的融資方式、融資平臺搭建聯系起來,才能形成政策的合力,把目前熱衷于做短期投機的資本集聚到新的融資平臺上,再反饋到產業(yè)上來。
要破題目前中國民間資本東奔西突、投機性強的問題,其實關鍵也就在這里。在民營經濟的發(fā)展上,溫州一直是一個先行者。通過金融改革,如果能夠把豐沛的民間資本引導好的話,那對于整個中國的民間資本的轉型發(fā)展都將產生示范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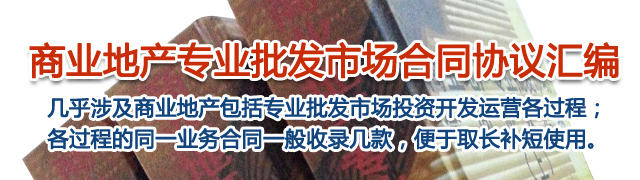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