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我們
聯系方式
老成都民間店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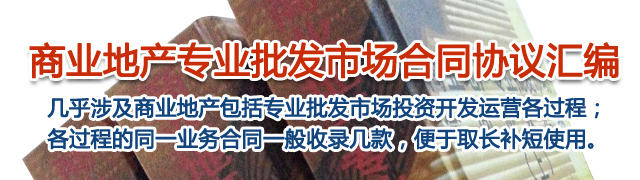 |
 |
五十年前的香油坊
今日紅星路步行街往右拐,到大慈寺以下一段,50年前分別叫湖廣館和棉花街,這兩條街都很熱鬧繁華,給我留下最獨特記憶的是兩條街交界處的一家香油坊。
50年代我在北打金街小學讀書,距“王者香”半條街,包里只要有一分錢,便去那兒買塊芝麻糖吃。芝麻糖香甜酥脆,好吃極了;還可免費聞聞隔壁香油坊的麻油飄香呀!那香味陣陣撲鼻,聞著舒坦愜意,快哉又樂哉,放學后貪玩的我在那兒消磨了不少的時光。
香油坊是雙間鋪面,鋪子左邊有個比現在立在街心太陽傘還大的石磨,石磨上有四支長長的粗粗的手柄。每天早上,四支手柄就是四個崗位,每個崗位站著一個瞎子,他們用肚子抵著手柄開始推磨。瞎子分老中青三代,一個老頭兒,兩個中年人,一個小伙子。他們肩上搭著條黑浸浸的毛巾,頭上用稻草系個圈兒擋汗。磨子緩緩地轉,發出均勻的嚓嚓聲響,四個瞎子翻看白眼很少說話,他們一步又一步,一圈又一圈,春夏秋冬,好似走著永無盡頭的人生步子。
年深日久,灰磚鋪就的地面已被他們踏成一圈淺淺的溝印。磨子上的芝麻堆積如小山,磨子底下置有一口大鐵鍋,推磨時芝麻從磨心輕緩地灌進,每推一圈,又稠又香的芝麻醬順著磨身一滴滴淌進鐵鍋。這時候,總有一個胖壯的中年女人坐在門口納鞋底,麻繩穿過鞋底嗖嗖作響。有人說她是老板娘,也有人說她是那個推磨的年輕瞎子的媳婦,她是個啞巴,到底是什么,我輩沒法搞清楚。
有好幾次我想問胖嬸嬸,怎么請瞎子推磨呢?但想她是啞巴只好作罷。有次我忘了她是啞巴,又悄悄地去問,沒想到她說話了,原來她不是啞巴,說北方推磨用毛驢蒙住眼睛打轉轉,川西壩子不產毛驢;并說如果眼睛看得見的人,推磨久了要發昏發暈,因而從祖上傳下來有請瞎子推磨的習俗。
說話間那口大鐵鍋的芝麻醬已快裝滿,并且移至屋中央,四個瞎子一人手執一個“長木瓜”在大鐵鍋中勞作。所謂長木瓜,是一個木制的球形體再裝上長柄,如古時的兵器。他們分四方站好,四支長木瓜在大鐵鍋內一陣陣翻滾、撥浪、提起、放下,所有的動作輕柔整齊。我發現是那個年輕的瞎子在指揮,叫喊了些聽不懂,但木瓜之舞太精彩,我和幾個小伙伴看得鼓起掌來。沒想到這下惹了禍,長木瓜頓然碰撞,發出幾聲哐哐的脆響,瞎子們嘎然停止,向上翻著白眼,那個年輕的瞎子大聲罵:“哪個龜兒子在亂叫喚!”我們如受驚的鳥兒一下散去。不多一會,我們又悄悄回香油坊,門口納鞋底的胖嬸嬸對我們說:“要看就好好看,不要鬧嘛!”
此時大鐵鍋內已浮上一層清亮淺黃的麻油,其中三個瞎子已停止勞作,只留下那個年輕瞎子“收關”。只見他口中念念有詞,木瓜在大鐵鍋內又轉又劃滾,像在書寫大字,又像在熨貼新衣,或變成一輛車在油面上飛掠而過……慢慢地油層越來越厚,香味越來越濃,麻醬和麻油明顯地分作兩層,醬狀物體往下沉,清亮的油像有泉眼往上涌……終于他停下了,坐在竹椅上抽葉子煙。
第二年冬末春初的日子,我放學后又去香油坊玩,卻不見了那個年輕瞎子,問胖嬸嬸,她說每年二月初二“龍抬頭”的日子,那瞎子便要站在他老家的山上,聽第一聲開雷。據說他爺爺也是瞎子,瞎了十多年,也就是二月初二這天一聲新雷,他爺爺的眼睛突然復明了!要等“龍抬頭”這天的開雷不容易啊!胖嬸嬸發出感嘆,但瞎子深信不疑,每年這天都在山口上等候……
記憶中的老成都日常生活
川主廟街雜貨店
據傳說,川主廟街建于明代崇禎元年(1628年),這條小小的街道,有茶鋪、商店、小吃等,其中街口的一家雜貨店,給我留下了難忘的記憶。
川主廟街與吟龍巷口相連,黑墻黑瓦的小巷左側就是川主廟街的李記雜貨店,雜貨店經營的是“油鹽醬醋”等雜貨,就是沒有茶。我給這家雜貨店的緣分,就是母親常叫我在這家雜貨店買“油鹽醬醋”,日子久了,與雜貨店李老板混熟了。
舊時,我家住在吟龍巷,離這家雜貨店不遠,走幾分鐘就能到雜貨店,記得那時,母親臨炒菜時,不是炒菜的青油沒了,就是鹽罐子見底,沒鹽了。“樹娃(我的小名)快點,買二兩青油回來炒菜!”“快點、買半斤鹽回來等到下鍋!”這是母親臨炒菜時,常叫我做到的事情。那時,我家較窮,父親去世,靠母親幫人洗衣服度日,家里燒的柴火,是在鄉間竹林撈的柴草煮飯,買油鹽醬醋,因錢不多,一次只能買二、三兩,吃的米是一天買一天。像我們這樣度日的平民百姓,那時在成都還不少。
記得,有天臨炒菜時,母親發現灶臺上的鹽罐子沒鹽了,照例叫我去買鹽,我飛奔雜貨店,叫李老板快點給包一包鹽。李老板與我開玩笑說:“我偏偏要慢!”其實,李老板心中有數,知道等著鹽下鍋,話還沒有說完,鹽已包好遞到我手上了。因母親等鹽下鍋,我非快往家跑,一不小心摔倒地上,把手中的鹽統統撒在地上了。我哭著回家,母親問我“鹽呢?”我不敢說真話,只曉得直哭,母親滅了灶臺中的火,拉著我去見雜貨店的李老板。母親問:“李老板,咋個的啊,我叫樹娃買鹽,鹽沒買回來,他直哭?”李老板說:“我知道你等鹽下鍋,很快就把鹽給樹娃了呀?”母親問我:“咋個回事呀?”我才老實說:“我摔倒了,把鹽撒在地上了!”母親伸手要打我,李老板拉著母親的手說:“算了,算了,樹娃還小,有點不懂事,我重新給你包一鹽,不收錢,快拿回去下鍋!”母親自然不肯,但鹽已遞到我手中,我拉著母親的手往家回,母親對李老板說:“下回把錢補給你!”
那些年,對我說來真是多事之秋,記得,有一天早晨,母親遲遲沒有起床,我在床前呼喚母親起床,可母親昏迷不醒,說不出話來。我慌了,準是母親得了病,咋辦?鄰居又沒有人,急得我團團轉。突然間,我想起了雜貨店的李老板,我跑步奔向雜貨店,李老板正要開門,我向他說明母親的情況,他聽后,把店門關上,說:“你快回去,照料母親,我去找臨街的醫生!”我回家后,母親仍然昏迷,嚇得我直哭。不多久,李老板帶來醫生到我家,醫生撿查后,說母親血壓太高。很危險。如果再晚點不吃藥,會引起腦溢血,后果就嚴重了。醫生開了藥,叫母親馬上吃,藥錢李老板給了。經過搶救治療,母親的病慢慢好了。后來,我把李老板找來醫生給母親治病的經過,擺給母親聽,母親聽后直說:“感謝恩人李老板啊!”
就這樣,我與雜貨店李老板,來來往往,度過了我的童年。解放后,我參加了工作。但川主廟街這家雜貨店不復存在了,李老板也不知去向。可我在這家雜貨店的緣分,特別是雜貨店的李老板的恩情,卻使我永生難忘。
干些賣風、火、煙、香的營生
舊茶館中的小買賣
舊日成都,是個生活節奏緩慢的消費城市,閑散的市民常去茶館消磨時日。茶館人一多,幾種不常見的小營生,便在那里應運而生,而所謂“賣風”,就是其中之一。
操此營生者必是一些窮苦人家的小孩,手持蒲扇一把。雖名曰“賣風”,實則是變相乞討。若茶客心好,或覺得扇舒服了,便會說聲:“行了,不扇了。”并付給一、兩分錢;如遇惡人,白扇了不說,討錢時還會挨罵:“滾開,看把老子都整感冒了!”
隨著季節變換,出沒于茶館的這些小孩當然不會老替人打扇。冬天一到,他們就統統拎上烤火的烘籠,開始“賣火”了。
老式茶館與時下燈光柔媚、簾幕低垂的茶坊不同,一般都是門敞窗開的,所以冬天特冷。人們去喝茶,一般都要帶上烘籠,手凍時烤手,腳冷時烤腳。但也有不帶的,特別是過路客人,手僵足冷時,只好向這些小孩租用烘籠了。租一只烘籠,烤半天(四小時左右),約須一個包子錢(五分),而那些乞兒去專門賣火的地方“撮”一烘籠火,卻只須一個饅頭錢(三分),雖有兩分錢的賺頭,但跑來跑去的,日子過得也艱難。更何況能讓你在茶館里討生活,對堂倌或店主的孝敬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忙上一冬,也僅能解決個人溫飽而已!
當然也有不止解決溫飽的營生,比如在茶館賣煙。而賣煙,當時又分為賣葉子煙、紙煙與賣水煙兩種。前者在胸前掛一只撮箕形的木匣,內裝各種紙煙和裹好的葉子煙,手持一根點煙的火繩,沿桌吆喝:“紙煙哇——葉子煙?點一支嘛!”紙煙也多是賣零支,一包煙分零后,有半包煙的利潤,葉子煙因系論斤稱來裹成一支支地買,利潤則更高!
最有趣是賣水煙。首先,那套裝備就扯眼球:一支牛皮大挎包鼓囊囊地吊在腰間,包內又有若干小格,分別裝著綿煙、黃絲、老口等品類不同的煙絲和一大束紙捻子。茶客要過癮了,只須手一揮,他們不但招之即來,奉上那碩大的、類如“薩克管”般的水煙袋,還要替客人裝煙、點火。吸煙者不僅可以不動手,甚至連頭都不用轉一下,就能在茶香裊裊中吞云吐霧了!
常言道:“不做無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人嘛,當你夏日在茶館享受了打扇,冬天在茶館烤夠了火,且又過足煙癮后,難免不生出一些非份之想。這時,你只需叫聲“堂倌——”并伸手向他作撫摸狀,精于此道的堂倌便心領神會。幾分鐘后,一張雪白的、熱乎乎的、且用香水灑得香噴噴的毛巾,便整齊方正疊在托盤里,呈到你面前,任你揩汗、抹臉或擦腳丫。“買香”是它的習稱,這種營生的全稱叫做“打香水帕子”或“賣香水帕子”。它與賣洗臉水、洗足水一樣,既是堂倌的專利,也是不用交柜,打烊后例由他們私分的外水錢……
老中醫何老頭說話模棱兩可
青石橋的草藥店
年齡在50歲左右的成都市民也許還記得,青石橋北街與東大街的拐角處,即現在的服裝批發市場,30年往前,是一所草藥店:不足百平米的兩層木樓內隔出三、四間簡陋的診室和候診、撿藥大廳,以清瘦矍爍的陳富春“陳草藥”領銜掛牌,小小診所經常是門庭若市,人員的走動使得木質樓板、地板顫悠悠的吱吱作響。病員多以兒童及老者居多,5分錢掛號,兩、三毛的藥錢,往往就能減輕人苦痛。
大約在1965年至1972年時段,小災小病時,我也去那里就診,但從未找過“王牌陳富春”,而是去等候那位個頭矮小、老眼昏花狀的“何老頭”問診。
何老頭清瘦、白皙,顫微微地伸出手搭在你的脈上,再用手扶一扶老花鏡,白眼端詳你的臉,讓你伸舌頭,捋袖取你手掌在姆指和食指間反復撫摩,認真看了,然后用濃重的川南地方音慢條斯理地發出系列問詢:
“你腦殼昏懂懂的?”
“你身上火巴嘰嘰的?”
“你周身蠕脹脹的?”
“你早遲咳竦竦的?”
“你腸胃不多余消受?”
然后就問你的飲食、睡眠、大小便;還問你的姓名、年齡、住址;然后用顫巍巍的手提筆抖動著在箋上開處方。
有人先恭敬遞上前次開的處方,訴說“已經松活多了”;再迎合老先生的問,把眉頭皺了;再附合著表現出“昏懂懂”、“蠕脹脹”、“咳竦竦”的難受情形,老先生就格外看得更仔細些。也有人慌忙報告完哪兒痛哪,敷衍著老先生不緊不慢、似有若無的問診,老先生就露出不解的神情,也許會在開方子時自言一句:“要過了下午些的時間,人就要松活些了。”
是說病情松活還是來看病的人數量松活,模棱兩可。
我去看病,卻從不那么著急,盡管在相對擁擠、劣質煙夾雜葉子煙味、咳喘聲伴隨唾痰聲的不良環境中,我依然入迷般咧開嘴,感受著木樓板嘎吱嘎吱地顫動,癡迷于何老頭淡定若閑的一招一式,但凡他老人家沒有使用他的慣用問診“套路”或有所省略,我便覺意猶未盡。而每每服用了他開出的處方,我的小疾便應藥而愈。遺憾的是,多少年過去了,回想起來,我竟只知道這位老先生的尊姓,卻沒有記下老人家的大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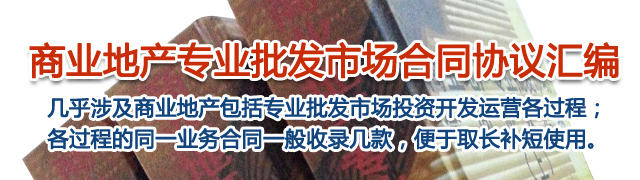 |
 |

